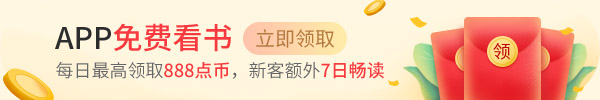3 3
我在不同的文體之間試來試去。
偶爾,某種嘗試會豁然打開儲藏,把它們化為火焰。每逢那種時刻到來,總是舍不得把雙手從鍵盤上拿開。不想錯過每一個能量爆發的玄妙時刻。一種可能性很快便會化為現實。
但我常常從秩序井然與娴熟中窺見一種表達方式的末路。手中的河流慢慢枯竭。到最後,河流成為紙上的标識,成為一道藍色的細線,成為一個概念。這意味着,并不是真正的源頭活水在吸引我,吸引我的隻是汛期造成的季節性的充沛。我跟我企圖呈現的事物之間依然是兩套肺腑。我擺脫不了我自己的慣性和偏見。
一位寫作者說,因為擔心這種隔離過早地發生,他于是返回故地,悉心體察那種曾經哺育過自己、如今已經十分隔膜的生活。他追尋着許多離鄉人的蹤迹,努力進入他們的日常,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在帶給他們什麼。他要求自己盡量忠實、整全地記錄。然而,幾年後他還是從紀實轉向了虛構。虛構中所蘊含的能量令人驚異。在題材與技法的雙重意義上,你都隻能夠看到它的來源,卻看不清它的終點。終點在地平線那邊。虛構的野心所指,在尋常視野之外。他還是以他捏合的“這一個”,代表了散布四方的他們。
也許,這正是另一種形式的撤離。
必須和有實質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離,我們的觀看才可能不失焦。我們身邊的人和事不是單純的人和事,而是一種含有過多成見的人際關系。過多地觸碰它們會有不可避免的困擾——你的傲慢與偏見,還有你的忌諱,都會自動過濾,造成散射、折射、逆光,造成隐瞞,造成失真的景象。
在屬于你的社區裡,坦誠是困難的。不曾有過徹底的坦誠,哪怕一次。你所有的陳詞隻不過貌似坦誠。你化妝之後才出門。你增加亮度,減去色斑。你把濃淡不一的兩條眉毛描畫得完全對稱。你使用逼近本色的绯聞唇釉。就是這樣,你紙上談兵,安排一場又一場沒有瑕疵的戰役。但那并不是真的戰役,沒有子彈穿梭,沒有流血與死亡。進而也沒有真正的危險,沒有身體面臨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脅時那種本能的不能自控的緊張,沒有膽怯與逃跑,沒有血淋淋的失敗,沒有屍橫遍野。也許這不能稱為撤離。這隻是逃脫,是從實質性的存在裡躲出去,在某個事不關己的角落裡,隔着防彈玻璃回頭看。
河流正在枯竭。并非智力或想象力的缺陷,而是感受力的萎靡。長久不遭遇強烈事物的感官正在喪失它們本來的敏銳。它們習慣于輕巧優雅的舒适,不痛不癢。唯有某些極端事件才能偶爾喚醒它們。
在偶爾醒來的片刻,我驚奇于自己的悲歡,它們新鮮而激烈,讓人不吐不快。極端事件的強烈和尖銳猶如一場私人世界的核裂變。我沒有靠近事件,但是事件穿透了我。事件很遠,無堅不摧的輻射依然穿牆而入,讓我的玻璃屏障失效。這種輻射常常帶來無可預見的破壞。在感受力短暫複蘇的劇痛中我不得不承認,所謂距離,就是隔閡。
“失焦”隻是一個假推論。我們的眼睛很少因為近在咫尺就失去焦點。在俗常“看”的意義上,失焦隻有在借助機械的情況下才存在。而在機械技術消除了微距攝影的困難之後,失焦似乎也就隻是一個與俗常之“看”無關的概念了。這樣“看”是不夠的。不投入其中你就永遠不能獲得真相。不投入其中,感受力就總是休眠,不能應和意志的調動。休眠是另一種死亡,是含有複蘇可能的淺死亡。
很晚以後才想明白,這根本不是遠近的問題,甚至也不是在場與否的問題。跟文體毫無關系。跟全部的手段毫無關系。這僅僅取決于一個人對自己的基本态度。在我和我的目的地之間,要麼冒險活着,要麼安穩睡着,沒有第三種可能。我的心意一直都沒有消除。我睡不着。
3
我在不同的文體之間試來試去。
偶爾,某種嘗試會豁然打開儲藏,把它們化為火焰。每逢那種時刻到來,總是舍不得把雙手從鍵盤上拿開。不想錯過每一個能量爆發的玄妙時刻。一種可能性很快便會化為現實。
但我常常從秩序井然與娴熟中窺見一種表達方式的末路。手中的河流慢慢枯竭。到最後,河流成為紙上的标識,成為一道藍色的細線,成為一個概念。這意味着,并不是真正的源頭活水在吸引我,吸引我的隻是汛期造成的季節性的充沛。我跟我企圖呈現的事物之間依然是兩套肺腑。我擺脫不了我自己的慣性和偏見。
一位寫作者說,因為擔心這種隔離過早地發生,他于是返回故地,悉心體察那種曾經哺育過自己、如今已經十分隔膜的生活。他追尋着許多離鄉人的蹤迹,努力進入他們的日常,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在帶給他們什麼。他要求自己盡量忠實、整全地記錄。然而,幾年後他還是從紀實轉向了虛構。虛構中所蘊含的能量令人驚異。在題材與技法的雙重意義上,你都隻能夠看到它的來源,卻看不清它的終點。終點在地平線那邊。虛構的野心所指,在尋常視野之外。他還是以他捏合的“這一個”,代表了散布四方的他們。
也許,這正是另一種形式的撤離。
必須和有實質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離,我們的觀看才可能不失焦。我們身邊的人和事不是單純的人和事,而是一種含有過多成見的人際關系。過多地觸碰它們會有不可避免的困擾——你的傲慢與偏見,還有你的忌諱,都會自動過濾,造成散射、折射、逆光,造成隐瞞,造成失真的景象。
在屬于你的社區裡,坦誠是困難的。不曾有過徹底的坦誠,哪怕一次。你所有的陳詞隻不過貌似坦誠。你化妝之後才出門。你增加亮度,減去色斑。你把濃淡不一的兩條眉毛描畫得完全對稱。你使用逼近本色的绯聞唇釉。就是這樣,你紙上談兵,安排一場又一場沒有瑕疵的戰役。但那并不是真的戰役,沒有子彈穿梭,沒有流血與死亡。進而也沒有真正的危險,沒有身體面臨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脅時那種本能的不能自控的緊張,沒有膽怯與逃跑,沒有血淋淋的失敗,沒有屍橫遍野。也許這不能稱為撤離。這隻是逃脫,是從實質性的存在裡躲出去,在某個事不關己的角落裡,隔着防彈玻璃回頭看。
河流正在枯竭。并非智力或想象力的缺陷,而是感受力的萎靡。長久不遭遇強烈事物的感官正在喪失它們本來的敏銳。它們習慣于輕巧優雅的舒适,不痛不癢。唯有某些極端事件才能偶爾喚醒它們。
在偶爾醒來的片刻,我驚奇于自己的悲歡,它們新鮮而激烈,讓人不吐不快。極端事件的強烈和尖銳猶如一場私人世界的核裂變。我沒有靠近事件,但是事件穿透了我。事件很遠,無堅不摧的輻射依然穿牆而入,讓我的玻璃屏障失效。這種輻射常常帶來無可預見的破壞。在感受力短暫複蘇的劇痛中我不得不承認,所謂距離,就是隔閡。
“失焦”隻是一個假推論。我們的眼睛很少因為近在咫尺就失去焦點。在俗常“看”的意義上,失焦隻有在借助機械的情況下才存在。而在機械技術消除了微距攝影的困難之後,失焦似乎也就隻是一個與俗常之“看”無關的概念了。這樣“看”是不夠的。不投入其中你就永遠不能獲得真相。不投入其中,感受力就總是休眠,不能應和意志的調動。休眠是另一種死亡,是含有複蘇可能的淺死亡。
很晚以後才想明白,這根本不是遠近的問題,甚至也不是在場與否的問題。跟文體毫無關系。跟全部的手段毫無關系。這僅僅取決于一個人對自己的基本态度。在我和我的目的地之間,要麼冒險活着,要麼安穩睡着,沒有第三種可能。我的心意一直都沒有消除。我睡不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