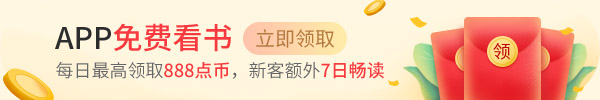2 2
塔尖在哪裡,也許從來都是不确定的。相對于文體,相對于執筆者,都是如此。
我記得她的随筆和評論。世界的精彩與頹敗、清純與混沌,竟可以表達得如此典雅、自由、準确——對我而言,這不僅是一種标高,更是一種緻命的吸引。閱讀中的我本是心眼俱冷,不容易被說服,更不容易被打動。因而,是否被說服、被打動,往往成為我對讀物的第一掂量。她的寫作使我确信文學意味着更多,确信文學不是或至少不僅是某種技藝高超的自洽,也不見得就是對與衆不同、流布四方的企望,或者,它隻是一種“與己不同”,是對這個局促的寄居之所的遊離,是明知不能擺脫卻懷着疏遠之心的告示。詩意其實早已、且似乎從來都可以彌漫于任何一種文體之中,隻要前提具備。詩意也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慫恿我們“撤離”的妄想。
幾年前的一個深秋,我跟随越野團隊去了黃河源頭。正當我在源頭界碑處駝色草甸上盯着水泊發呆的時候,天氣突變。我看見青色水泊瞬間變成灰白,繼而變成鐵黑。擡頭一看,墨黑的烏雲正從高空翻滾而下。高原上的雲有觸目的質感,它們正在下落,很快,很重,仿佛那不是雲團,而是大塊大塊的含鹽的海水,它自上而下砸向我,像一場從天而降的海嘯。那情景讓人心驚肉跳。我們轉身奔向停在路邊的越野車,迅速發動,掉頭,上路。越野車沿着駝色草甸上的土路倉皇逃離。雲層還在往下壓。大片的駝色草坡與鐵黑的雲層形成炫目的撞色,有一種令人魂飛魄散的美。我記得就在那時,草坡低緩處忽然出現了一群藏野驢——有六七隻。它們對那樣的天氣突變仿佛無感,仍然在草坡上悠閑地吃草。那悠閑傳遞了一種令人放心的訊号,瞬間緩解了我的緊張。我記得那時景象奇異。車前車後是東邊日出西邊雨的強烈對比,頭頂是陸地般的雲層,遠處地平線之上是一線炫目的晴空。我感覺雲層像是某種正在經過頭頂的地質平移物,一片滑翔中的天空之城,或者固體的大海。
大雪是在我們經過漫水灘的時候來的。眨眼之間,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。進來時依稀可辨的土路完全不見蹤迹。我腦際掠過許多人寫過唱過吟誦過的黃河源,想到一位李姓畫家的長卷,也想到她那篇著名的随筆。那時我搭乘的越野車裡正放着刀郎的《西海情歌》。那首歌的創作源自一樁絕戀:一對大學畢業的戀人一同報名,志願到寂寥的可可西裡去。女孩被安排到藏羚羊觀察站,男孩則被安排到條件更加艱苦的沱沱河觀察站。不久,男孩被一場大雪困住,不幸凍死在可可西裡腹地。不知道這個故事,就不太可能體會歌聲裡的悲痛。
對那種逼近絕對的美感和荒涼,這個正在聊着詩歌、略有疲倦之色的人,曾以随筆的形式表達過。
那一年深秋,在黃河源漫水灘的雪地裡,他們有過的悲痛也映現到我心頭。我想起那個素不相識的葬身可可西裡的男孩,想起若幹年前帶着測繪儀器随隊來過此地的父親,想起那個執意奔赴雪山的野人,在那片去路蒼茫的漫水灘上,悲痛有如眼前的雪原一樣無邊無際。那是别人的悲痛,也是我的。是我的,仿佛也是許多人的。許多人,那些跟我相關或不相關的人,今人古人,男人女人,他們的故事層層疊疊,在我頭頂形成巨大的令人驚怖的懸念。
我們心中的全部感想,我們全部的記憶和想象,相對于現實的發生,總還是顯得孱弱,窄小,輕浮。在生死愛恨的大事件之間,更多的是無止無休的日常。就如江河,源流蕪雜,循環往複。
局限于方寸之間的寫作,似乎與這樣的分量不吻合,不匹配。令人意難平。
2
塔尖在哪裡,也許從來都是不确定的。相對于文體,相對于執筆者,都是如此。
我記得她的随筆和評論。世界的精彩與頹敗、清純與混沌,竟可以表達得如此典雅、自由、準确——對我而言,這不僅是一種标高,更是一種緻命的吸引。閱讀中的我本是心眼俱冷,不容易被說服,更不容易被打動。因而,是否被說服、被打動,往往成為我對讀物的第一掂量。她的寫作使我确信文學意味着更多,确信文學不是或至少不僅是某種技藝高超的自洽,也不見得就是對與衆不同、流布四方的企望,或者,它隻是一種“與己不同”,是對這個局促的寄居之所的遊離,是明知不能擺脫卻懷着疏遠之心的告示。詩意其實早已、且似乎從來都可以彌漫于任何一種文體之中,隻要前提具備。詩意也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慫恿我們“撤離”的妄想。
幾年前的一個深秋,我跟随越野團隊去了黃河源頭。正當我在源頭界碑處駝色草甸上盯着水泊發呆的時候,天氣突變。我看見青色水泊瞬間變成灰白,繼而變成鐵黑。擡頭一看,墨黑的烏雲正從高空翻滾而下。高原上的雲有觸目的質感,它們正在下落,很快,很重,仿佛那不是雲團,而是大塊大塊的含鹽的海水,它自上而下砸向我,像一場從天而降的海嘯。那情景讓人心驚肉跳。我們轉身奔向停在路邊的越野車,迅速發動,掉頭,上路。越野車沿着駝色草甸上的土路倉皇逃離。雲層還在往下壓。大片的駝色草坡與鐵黑的雲層形成炫目的撞色,有一種令人魂飛魄散的美。我記得就在那時,草坡低緩處忽然出現了一群藏野驢——有六七隻。它們對那樣的天氣突變仿佛無感,仍然在草坡上悠閑地吃草。那悠閑傳遞了一種令人放心的訊号,瞬間緩解了我的緊張。我記得那時景象奇異。車前車後是東邊日出西邊雨的強烈對比,頭頂是陸地般的雲層,遠處地平線之上是一線炫目的晴空。我感覺雲層像是某種正在經過頭頂的地質平移物,一片滑翔中的天空之城,或者固體的大海。
大雪是在我們經過漫水灘的時候來的。眨眼之間,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。進來時依稀可辨的土路完全不見蹤迹。我腦際掠過許多人寫過唱過吟誦過的黃河源,想到一位李姓畫家的長卷,也想到她那篇著名的随筆。那時我搭乘的越野車裡正放着刀郎的《西海情歌》。那首歌的創作源自一樁絕戀:一對大學畢業的戀人一同報名,志願到寂寥的可可西裡去。女孩被安排到藏羚羊觀察站,男孩則被安排到條件更加艱苦的沱沱河觀察站。不久,男孩被一場大雪困住,不幸凍死在可可西裡腹地。不知道這個故事,就不太可能體會歌聲裡的悲痛。
對那種逼近絕對的美感和荒涼,這個正在聊着詩歌、略有疲倦之色的人,曾以随筆的形式表達過。
那一年深秋,在黃河源漫水灘的雪地裡,他們有過的悲痛也映現到我心頭。我想起那個素不相識的葬身可可西裡的男孩,想起若幹年前帶着測繪儀器随隊來過此地的父親,想起那個執意奔赴雪山的野人,在那片去路蒼茫的漫水灘上,悲痛有如眼前的雪原一樣無邊無際。那是别人的悲痛,也是我的。是我的,仿佛也是許多人的。許多人,那些跟我相關或不相關的人,今人古人,男人女人,他們的故事層層疊疊,在我頭頂形成巨大的令人驚怖的懸念。
我們心中的全部感想,我們全部的記憶和想象,相對于現實的發生,總還是顯得孱弱,窄小,輕浮。在生死愛恨的大事件之間,更多的是無止無休的日常。就如江河,源流蕪雜,循環往複。
局限于方寸之間的寫作,似乎與這樣的分量不吻合,不匹配。令人意難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