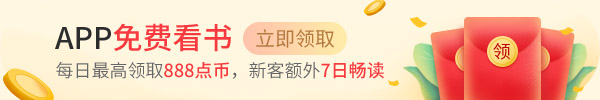2 2
父親的忌日在農曆小滿前後,正是蠶蛹結繭,桑葚成熟,小麥灌漿的時節。布谷鳥正在嘹亮地鳴叫,空氣裡飄蕩着新鮮果木的香氣,一切景象都顯得祥和。我在麥田裡。麥子莖稈青碧,從根到梢都是濕的。還可以坐在墳頭邊的田壟上抽支煙,而不必擔心會引燃一片葉子。一次點兩支煙,墳頭放一支,我抽一支。我們都不是沉默寡言的人,但我極少跟他長篇大論地說話。不習慣。好在還有煙。想說什麼總會有憑借的。煙就是憑借——他抽完了,你也抽完了,就再來一支,根本不用廢話。
父親的“不在”,在煙的氣息裡變得更其确鑿。
早年把世事看得輕易,目光總是投向遠處,顧不上細細琢磨沿途的遇合,也不曾十分重視他的“在”。父親的“在”是一種不需要論證的公理,是從我們出生就已經先在的、可以随時援引的前提,是人生一切推導無須明言的依據。那種“在”,不是生命裡偶然介入的元素,不會特别引起注意,仿佛他會一直“在”那兒,理所當然,不需要條件。然而有一天,“在”的條件被命運剝落,我們的公理被搖撼,進而被推翻——那個人,他“不在”了。
回家也不再能夠接近他。“不在”布滿了院子。在形式上,這個被叫作“家”的地方一切如故。院子與幾年前一模一樣,街巷也一模一樣,門口還放着他喜歡坐的青石闆,影壁前的蘋果樹上,他修剪鳳凰棵。留下的斧痕曆曆如新。隻是那個人不在了。“不在”成為被謎團包裹的刀刃,寒凜凜的,卻無從捉摸。父親的歡迎也已“不在”。這個家裡,兄弟姐妹加上他們的丈夫妻子和孩子,烏泱烏泱一屋子人。他們大多健談,喜歡高聲大嗓、排山倒海地說話。這熱鬧是空心的,無趣,令人生厭。在沸沸揚揚的語音裡,父親的曾“在”如同虛拟——在大腦的記錄中确實有,卻仿佛并沒有在時間之内發生過。我在沸沸揚揚的語音裡發呆。我這個人,我的懷念,俱如虛拟。
“回家”成為庸常時日中格外凸出的部分,成為一根刺。我們都回來了,但是團聚永遠不會有了。我甚至也不敢為家人拍照。這麼些年,我的取景框裡人總是不全,不是這個回不來,就是那個回不來。如今有個人永遠回不來了,我的取景框再也不可能取到一張全家福了。
有過最難挨的一段時間。我能夠做的似乎唯有上路,不停地奔走。媽在伊城,豫北老家并沒有誰等着我回去,這樣的長途奔襲顯得毫無理由,我還是莫名其妙地要驅車上路,向那個方向開過去。偶爾,車到中途便停住了,有如被某種巨大的理由陡然攔阻。我開下高速,漫無目的地拐上鄉間公路,在蕩起的塵土中穿過一個又一個村莊。不知道究竟要開到哪裡才是窮途,才願意停下來号啕一場,然後返回。沿途的景象似是而非,與我充滿了隔閡。
不在就是不在了,一點痕迹都看不到。這無可挽回的“不在”,是我遇到的第一件無力消化的事。我本來以為,父親的離開雖然令人悲痛,但隻是人生必須接受的事件之一。不是嗎?父親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永在的角色,他會變老,會生病,會突然從我的生命場域中撤離。這完全出乎意料——最初心情近乎麻木,甚至有略微的輕松,仿佛随着他的離開,他解脫了,我也解脫了;接着便寂若真空;然後,那種情緒才慢慢襲來。心裡壅塞的是一些垂墜之物,斑駁雜陳,類若哀恸,又不純淨,仿佛哀恸留下的渣滓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,我陷入了沼澤般的虛無。
祭奠儀式太多了。祭奠先是每周一次,然後是百天,還有一兩個月就會到來的鬼節,然後是周年,一周年,兩周年,三周年。那些壅塞物,好容易按捺下去,又一再被翻攪上來。擺在靈位前的供奉令人難受。供奉越豐盛,看着越讓人難受。他不需要這些了。他的肉身已經化為泥土,什麼也不需要了。我們的供奉隻是給自己的安慰。他也不會再有期待。從今以後,我們即或有所成就,也隻是給自己的了。成就與我們的生命背景相脫離,失去了本來的重量,變得輕浮,功利,像一樁将要在街市上發生的交易。是吧,你也知道的,這種堕落僅僅在你這裡發生,卻不是你造成的……許多時候你隻能端起酒杯,喝一口,再喝一口,喝到發呆。
烈酒入喉,隻是釀成了倦怠和昏迷,壅塞物并沒有清除。它高聳而且迫近,就像王屋橫亘,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崩解。我懷疑是不是因為說得太早了。我還沒有消化,就經不得折磨,把這痛楚全部招供。這樣“說出”,等于貿然拆穿了一樁秘事。是否那種膚淺的絮叨破壞了内部蘊藏的勢能,進而,需要諱言以敬才會清晰呈現的命運,就此改弦更張?我走在路上,沉默或者号啕,卻不能回答。
那個岔口,就在京珠高速與淇北街交叉口的高架橋東側,因為不被注意,缺少維護,因而崎岖難行。岔口向西,是筆直寬闊的柏油路;向東北,則是勉強可以錯車的鄉間公路。鄉間公路沒有名字,為了稱呼它,我名之為泉源路。《詩經·衛風》為憑:
籊籊竹竿,以釣于淇。
豈不爾思?遠莫緻之。
泉源在左,淇水在右。
女子有行,遠兄弟父母。
我的故鄉曾有河流貫穿,河名“翟泉”。詩句裡的“籊”,雖與“翟”字音義俱異,但我依然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們在辭源上是有聯系的,詩中的“泉源”就是與淇水有源流關系的翟泉。每次經過那個岔口,我便會條件反射般想起“泉源在左,淇水在右”的句子,認定這岔口必是那遠行女子思念中的故地。
奇怪的是,家鄉沒有人知道貫穿村莊的小河叫作翟泉河。翟泉河這個名字的來龍去脈早已失傳。這個名字也将失傳。沒有人關心一條已經幹涸了的河流。
在淇水與泉源之間長大的女兒,十幾歲遠離故土,不是因為出嫁,而是因為求學。這遠行一如溪流入河,河流入海,不惟離源頭越來越遠,連源頭的清澈也一并喪失。若幹年後,我也成了一個慣于四處奔襲、獨自遊蕩的人,類如車至窮途、大哭而返的阮籍。窮途——那莫可名狀的阻斷與隔閡,“惜逝忽若浮”的況味,現在我也體會了。它一點也不詩意,沒有重量,沒有形狀,有如強大的磁場,吸住誰,誰就難以掙脫。我一趟一趟返回,恍若在竭力靠近一樁懸念。
許多寫作的人,都有一個放不下的故事。他可能寫過千百個故事,但是其中的一個,總也完不成。他寫了劄記寫故事,寫了短篇寫長篇,寫了正文寫補錄,挖掘,翻檢,反反複複,無休無止。某個故事,發生在某時某地的故事,他總也不收手。他總想看清楚——看得見源頭,後來發生的一切才能迎刃而解。
那個總是在的。它意味着這個人是誰,而不是經過質變或雜糅,成為誰。那也是必然要回去的地方。可以佯裝無視,但任何一種天然聯結,都不可能被昧滅。某個時刻,在往事的鏡前,沿途所遇的問題蓦然澄清,你也會的,在這面深不見底的往事的鏡前,你也會滿懷驚詫與憐憫地打量你自己。
2
父親的忌日在農曆小滿前後,正是蠶蛹結繭,桑葚成熟,小麥灌漿的時節。布谷鳥正在嘹亮地鳴叫,空氣裡飄蕩着新鮮果木的香氣,一切景象都顯得祥和。我在麥田裡。麥子莖稈青碧,從根到梢都是濕的。還可以坐在墳頭邊的田壟上抽支煙,而不必擔心會引燃一片葉子。一次點兩支煙,墳頭放一支,我抽一支。我們都不是沉默寡言的人,但我極少跟他長篇大論地說話。不習慣。好在還有煙。想說什麼總會有憑借的。煙就是憑借——他抽完了,你也抽完了,就再來一支,根本不用廢話。
父親的“不在”,在煙的氣息裡變得更其确鑿。
早年把世事看得輕易,目光總是投向遠處,顧不上細細琢磨沿途的遇合,也不曾十分重視他的“在”。父親的“在”是一種不需要論證的公理,是從我們出生就已經先在的、可以随時援引的前提,是人生一切推導無須明言的依據。那種“在”,不是生命裡偶然介入的元素,不會特别引起注意,仿佛他會一直“在”那兒,理所當然,不需要條件。然而有一天,“在”的條件被命運剝落,我們的公理被搖撼,進而被推翻——那個人,他“不在”了。
回家也不再能夠接近他。“不在”布滿了院子。在形式上,這個被叫作“家”的地方一切如故。院子與幾年前一模一樣,街巷也一模一樣,門口還放着他喜歡坐的青石闆,影壁前的蘋果樹上,他修剪鳳凰棵。留下的斧痕曆曆如新。隻是那個人不在了。“不在”成為被謎團包裹的刀刃,寒凜凜的,卻無從捉摸。父親的歡迎也已“不在”。這個家裡,兄弟姐妹加上他們的丈夫妻子和孩子,烏泱烏泱一屋子人。他們大多健談,喜歡高聲大嗓、排山倒海地說話。這熱鬧是空心的,無趣,令人生厭。在沸沸揚揚的語音裡,父親的曾“在”如同虛拟——在大腦的記錄中确實有,卻仿佛并沒有在時間之内發生過。我在沸沸揚揚的語音裡發呆。我這個人,我的懷念,俱如虛拟。
“回家”成為庸常時日中格外凸出的部分,成為一根刺。我們都回來了,但是團聚永遠不會有了。我甚至也不敢為家人拍照。這麼些年,我的取景框裡人總是不全,不是這個回不來,就是那個回不來。如今有個人永遠回不來了,我的取景框再也不可能取到一張全家福了。
有過最難挨的一段時間。我能夠做的似乎唯有上路,不停地奔走。媽在伊城,豫北老家并沒有誰等着我回去,這樣的長途奔襲顯得毫無理由,我還是莫名其妙地要驅車上路,向那個方向開過去。偶爾,車到中途便停住了,有如被某種巨大的理由陡然攔阻。我開下高速,漫無目的地拐上鄉間公路,在蕩起的塵土中穿過一個又一個村莊。不知道究竟要開到哪裡才是窮途,才願意停下來号啕一場,然後返回。沿途的景象似是而非,與我充滿了隔閡。
不在就是不在了,一點痕迹都看不到。這無可挽回的“不在”,是我遇到的第一件無力消化的事。我本來以為,父親的離開雖然令人悲痛,但隻是人生必須接受的事件之一。不是嗎?父親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永在的角色,他會變老,會生病,會突然從我的生命場域中撤離。這完全出乎意料——最初心情近乎麻木,甚至有略微的輕松,仿佛随着他的離開,他解脫了,我也解脫了;接着便寂若真空;然後,那種情緒才慢慢襲來。心裡壅塞的是一些垂墜之物,斑駁雜陳,類若哀恸,又不純淨,仿佛哀恸留下的渣滓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,我陷入了沼澤般的虛無。
祭奠儀式太多了。祭奠先是每周一次,然後是百天,還有一兩個月就會到來的鬼節,然後是周年,一周年,兩周年,三周年。那些壅塞物,好容易按捺下去,又一再被翻攪上來。擺在靈位前的供奉令人難受。供奉越豐盛,看着越讓人難受。他不需要這些了。他的肉身已經化為泥土,什麼也不需要了。我們的供奉隻是給自己的安慰。他也不會再有期待。從今以後,我們即或有所成就,也隻是給自己的了。成就與我們的生命背景相脫離,失去了本來的重量,變得輕浮,功利,像一樁将要在街市上發生的交易。是吧,你也知道的,這種堕落僅僅在你這裡發生,卻不是你造成的……許多時候你隻能端起酒杯,喝一口,再喝一口,喝到發呆。
烈酒入喉,隻是釀成了倦怠和昏迷,壅塞物并沒有清除。它高聳而且迫近,就像王屋橫亘,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崩解。我懷疑是不是因為說得太早了。我還沒有消化,就經不得折磨,把這痛楚全部招供。這樣“說出”,等于貿然拆穿了一樁秘事。是否那種膚淺的絮叨破壞了内部蘊藏的勢能,進而,需要諱言以敬才會清晰呈現的命運,就此改弦更張?我走在路上,沉默或者号啕,卻不能回答。
那個岔口,就在京珠高速與淇北街交叉口的高架橋東側,因為不被注意,缺少維護,因而崎岖難行。岔口向西,是筆直寬闊的柏油路;向東北,則是勉強可以錯車的鄉間公路。鄉間公路沒有名字,為了稱呼它,我名之為泉源路。《詩經·衛風》為憑:
籊籊竹竿,以釣于淇。
豈不爾思?遠莫緻之。
泉源在左,淇水在右。
女子有行,遠兄弟父母。
我的故鄉曾有河流貫穿,河名“翟泉”。詩句裡的“籊”,雖與“翟”字音義俱異,但我依然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們在辭源上是有聯系的,詩中的“泉源”就是與淇水有源流關系的翟泉。每次經過那個岔口,我便會條件反射般想起“泉源在左,淇水在右”的句子,認定這岔口必是那遠行女子思念中的故地。
奇怪的是,家鄉沒有人知道貫穿村莊的小河叫作翟泉河。翟泉河這個名字的來龍去脈早已失傳。這個名字也将失傳。沒有人關心一條已經幹涸了的河流。
在淇水與泉源之間長大的女兒,十幾歲遠離故土,不是因為出嫁,而是因為求學。這遠行一如溪流入河,河流入海,不惟離源頭越來越遠,連源頭的清澈也一并喪失。若幹年後,我也成了一個慣于四處奔襲、獨自遊蕩的人,類如車至窮途、大哭而返的阮籍。窮途——那莫可名狀的阻斷與隔閡,“惜逝忽若浮”的況味,現在我也體會了。它一點也不詩意,沒有重量,沒有形狀,有如強大的磁場,吸住誰,誰就難以掙脫。我一趟一趟返回,恍若在竭力靠近一樁懸念。
許多寫作的人,都有一個放不下的故事。他可能寫過千百個故事,但是其中的一個,總也完不成。他寫了劄記寫故事,寫了短篇寫長篇,寫了正文寫補錄,挖掘,翻檢,反反複複,無休無止。某個故事,發生在某時某地的故事,他總也不收手。他總想看清楚——看得見源頭,後來發生的一切才能迎刃而解。
那個總是在的。它意味着這個人是誰,而不是經過質變或雜糅,成為誰。那也是必然要回去的地方。可以佯裝無視,但任何一種天然聯結,都不可能被昧滅。某個時刻,在往事的鏡前,沿途所遇的問題蓦然澄清,你也會的,在這面深不見底的往事的鏡前,你也會滿懷驚詫與憐憫地打量你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