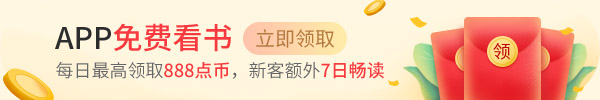寄居之所 寄居之所
1
她坐在那裡說話,聲音很輕。後面的人聽不清楚。有人把話筒向她嘴邊移近了一點。聲音依然很輕。那是後退的、雲淡風輕的聲音,獨白的口吻,仿佛她面對的不是人群,而是一片空地。
這是一場以詩歌為主題的讀書會。她聊起自己詩歌的精神來源,聊到索德格朗,辛波斯卡,狄金森。也都是我喜愛的。女性對于生命的獨特直覺在詩歌裡曾經得到過怎樣的表達,從她們便可窺見。這種吸納與輸出的力量是軟性的、強韌的,正如水流,仿佛渙散,可以随物賦形,卻能浸透許多事物。
她描述那座創造力的金字塔。她說她曾把文藝輸出中最為理性的部分視為塔尖。當一種觀念廣被認可之後,理念便成為新構築的塔基,進而,一個倒過來的金字塔出現了。這時候,塔尖是詩歌。這種困難度最高的表達形式,考驗的不僅僅是語言,更是整全的人格,需要調動整體的生命經驗。她說,正是這種高度和完成度,讓她在人生最困難的時期重新選擇了詩歌,而詩歌也成為拯救者。
人們開始發言。我細聽他們說話,覺得他們并不怎麼關心詩歌。他們更關心她這個人——他們和她的交道,她的才華,她的成就。這關心有點複雜,有點枝枝蔓蔓,跟她正在聊的話題不大貼合。在座者有許多人跟她是舊相識。老友相見,能把任何話題變成叙舊,這很正常。座中有些人曾經寫過詩歌,後來轉向了别的文體。和其他行業一樣,詩歌當然也可以被視為由從業者構成的行當。從業者會漸漸形成一個圈子,但似乎隻有極少數在意詩歌,大多數對詩歌不以為意。對許多人而言,“寫詩”仿佛是對某個行當的投靠。但詩歌屬于極端的事物,需要極端的心腸,大冷或者大熱。這是具有奇異禀賦的一小撮人的事,甚至,有時候我想,詩歌簡直是非人間的事,隻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。
她不怎麼答問,隻是自說自話。一個人沒有輾轉四顧的習慣,自然會保持這樣的态度——你們關心你們的,我關心我的,我不需要你們附和我,我的注意力也不會被你們牽着走。
我跟她至多屬于熟人,還算不上朋友。事實上,由于開始寫作很晚,我跟圈中許多人都沒有過深的交道。偶爾在飯局上聽見些零零星星的掌故,關于張三,關于李四,因為沒有直接經驗做依據,頗覺難辨真僞。在影影綽綽的流言裡,寫詩的人多少有點不尋常,會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,說一些匪夷所思的話。有時候陷在傳聞所提供的場景裡,我想象當時的細節,很難像别人一樣笑出聲來。我左想想右想想,會把我這個不寫詩的人也想進去。我也會的,會在那種情形中突然感到厭惡,會說出冰淩般的冷話。這本是尋常人情,不難理解。隻是人們習慣于對某些行當抱持苛求。
我也是不謹慎的人,容易受到流言攻擊。常常是這樣,一樁關于你的流言已經到處流傳,你才在某個角落不經意間聽到。流言并不面目可憎,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傳播的。在貌似并無惡意的嬉笑聲裡,一個“被談論的人”會無端成為可笑之人。
沒有什麼比“滑稽”更能瓦解詩意了。無論如何,詩歌之事總是莊重的;詩人,可以霸道,好色,神經質,但不能是個小醜——這是人們心中的定律。要擺脫種種歧義和框定,對人來說是困難的,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她似乎一直能跟這些瑣屑之事保持距離。仿佛她有一層隔離灰塵的隐身衣,這些人際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。
在舉辦書會的園子裡,女人們照例花枝招展,讓人想到莺莺燕燕這樣的描述。而她簡單到底。一頭不加修飾的短發,一襲暗紅羊絨長外套,平底卡其色皮鞋。即便在室外,她說話音量也不高,雙手籠在衣袋裡慢悠悠走路,極少大笑,從不勾肩搭背。我就想,這是個不會跟任何人過從甚密的人。就人際交往的規律來看也缺乏這種可能。精神自足會讓一個人意識到人和人保持間距的重要。或者可以說,間距不見得被明确意識到,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,它會在主客之間——在自我與他人、自我與外物之間,拉開一個恰當的距離。
這讓我羨慕。也因此,我先看她怎麼個“撤離”。眼前這本書輯錄的詩歌全部寫于前一年。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。對她而言,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紀。詩行裡的撤離仿佛是忍耐許久之後所下的一個決心,是破釜沉舟式的,毅然,徹底,絕無猶疑。漫長的排比猶如閱兵式上的隊列行進,整齊,隆重,氣勢如虹。在這樣的形式之中卻又藏着肅殺,令人感受到某種一意孤行的壯烈。這種骨子裡的堅決,慨當以慷的氣概,也許正是漢語詩歌特有的美感之一。
與生命的險峻所抗衡的轉身,難免帶有強烈的儀式感。所有目不斜視的孤絕的吟誦者,也許都是這樣的。盡管我對這易水歌般的決絕懷有仰慕,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,至少對尋常人而言,從一切中撤離,并不是憑一次決意就可以實現。這束縛了我們,也給予我們寄居之所的外殼——身體,以及維護這個寄居之所所必需的事物,如果不是由于閱讀與寫作,如果不是由于詩歌或詩意,那些具體事物所構成的小世界,或許就是我們全部的命運;如果不是由于我們心有旁骛,或許這外殼終将令我們俯首帖耳。
寄居之所
1
她坐在那裡說話,聲音很輕。後面的人聽不清楚。有人把話筒向她嘴邊移近了一點。聲音依然很輕。那是後退的、雲淡風輕的聲音,獨白的口吻,仿佛她面對的不是人群,而是一片空地。
這是一場以詩歌為主題的讀書會。她聊起自己詩歌的精神來源,聊到索德格朗,辛波斯卡,狄金森。也都是我喜愛的。女性對于生命的獨特直覺在詩歌裡曾經得到過怎樣的表達,從她們便可窺見。這種吸納與輸出的力量是軟性的、強韌的,正如水流,仿佛渙散,可以随物賦形,卻能浸透許多事物。
她描述那座創造力的金字塔。她說她曾把文藝輸出中最為理性的部分視為塔尖。當一種觀念廣被認可之後,理念便成為新構築的塔基,進而,一個倒過來的金字塔出現了。這時候,塔尖是詩歌。這種困難度最高的表達形式,考驗的不僅僅是語言,更是整全的人格,需要調動整體的生命經驗。她說,正是這種高度和完成度,讓她在人生最困難的時期重新選擇了詩歌,而詩歌也成為拯救者。
人們開始發言。我細聽他們說話,覺得他們并不怎麼關心詩歌。他們更關心她這個人——他們和她的交道,她的才華,她的成就。這關心有點複雜,有點枝枝蔓蔓,跟她正在聊的話題不大貼合。在座者有許多人跟她是舊相識。老友相見,能把任何話題變成叙舊,這很正常。座中有些人曾經寫過詩歌,後來轉向了别的文體。和其他行業一樣,詩歌當然也可以被視為由從業者構成的行當。從業者會漸漸形成一個圈子,但似乎隻有極少數在意詩歌,大多數對詩歌不以為意。對許多人而言,“寫詩”仿佛是對某個行當的投靠。但詩歌屬于極端的事物,需要極端的心腸,大冷或者大熱。這是具有奇異禀賦的一小撮人的事,甚至,有時候我想,詩歌簡直是非人間的事,隻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。
她不怎麼答問,隻是自說自話。一個人沒有輾轉四顧的習慣,自然會保持這樣的态度——你們關心你們的,我關心我的,我不需要你們附和我,我的注意力也不會被你們牽着走。
我跟她至多屬于熟人,還算不上朋友。事實上,由于開始寫作很晚,我跟圈中許多人都沒有過深的交道。偶爾在飯局上聽見些零零星星的掌故,關于張三,關于李四,因為沒有直接經驗做依據,頗覺難辨真僞。在影影綽綽的流言裡,寫詩的人多少有點不尋常,會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,說一些匪夷所思的話。有時候陷在傳聞所提供的場景裡,我想象當時的細節,很難像别人一樣笑出聲來。我左想想右想想,會把我這個不寫詩的人也想進去。我也會的,會在那種情形中突然感到厭惡,會說出冰淩般的冷話。這本是尋常人情,不難理解。隻是人們習慣于對某些行當抱持苛求。
我也是不謹慎的人,容易受到流言攻擊。常常是這樣,一樁關于你的流言已經到處流傳,你才在某個角落不經意間聽到。流言并不面目可憎,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傳播的。在貌似并無惡意的嬉笑聲裡,一個“被談論的人”會無端成為可笑之人。
沒有什麼比“滑稽”更能瓦解詩意了。無論如何,詩歌之事總是莊重的;詩人,可以霸道,好色,神經質,但不能是個小醜——這是人們心中的定律。要擺脫種種歧義和框定,對人來說是困難的,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她似乎一直能跟這些瑣屑之事保持距離。仿佛她有一層隔離灰塵的隐身衣,這些人際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。
在舉辦書會的園子裡,女人們照例花枝招展,讓人想到莺莺燕燕這樣的描述。而她簡單到底。一頭不加修飾的短發,一襲暗紅羊絨長外套,平底卡其色皮鞋。即便在室外,她說話音量也不高,雙手籠在衣袋裡慢悠悠走路,極少大笑,從不勾肩搭背。我就想,這是個不會跟任何人過從甚密的人。就人際交往的規律來看也缺乏這種可能。精神自足會讓一個人意識到人和人保持間距的重要。或者可以說,間距不見得被明确意識到,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,它會在主客之間——在自我與他人、自我與外物之間,拉開一個恰當的距離。
這讓我羨慕。也因此,我先看她怎麼個“撤離”。眼前這本書輯錄的詩歌全部寫于前一年。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。對她而言,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紀。詩行裡的撤離仿佛是忍耐許久之後所下的一個決心,是破釜沉舟式的,毅然,徹底,絕無猶疑。漫長的排比猶如閱兵式上的隊列行進,整齊,隆重,氣勢如虹。在這樣的形式之中卻又藏着肅殺,令人感受到某種一意孤行的壯烈。這種骨子裡的堅決,慨當以慷的氣概,也許正是漢語詩歌特有的美感之一。
與生命的險峻所抗衡的轉身,難免帶有強烈的儀式感。所有目不斜視的孤絕的吟誦者,也許都是這樣的。盡管我對這易水歌般的決絕懷有仰慕,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,至少對尋常人而言,從一切中撤離,并不是憑一次決意就可以實現。這束縛了我們,也給予我們寄居之所的外殼——身體,以及維護這個寄居之所所必需的事物,如果不是由于閱讀與寫作,如果不是由于詩歌或詩意,那些具體事物所構成的小世界,或許就是我們全部的命運;如果不是由于我們心有旁骛,或許這外殼終将令我們俯首帖耳。